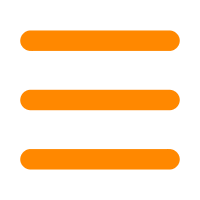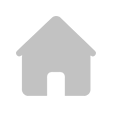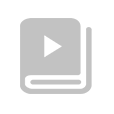欧洲国内国家14—16世纪时出现了三R现象:一是文静复兴(Renaissance);一是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一是罗马法复兴(RecoveryofRomanLaw)。三个方面虽然不同,但集中一点是人文主义的胜
利。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由得到了承认和解放。
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步,中国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是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
以说市场经济的打造和进步也势必需要罗马法精神的复兴,当然绝不可能是两千年前西方古典法律规范在中
国的重现和恢复。那样,应当如何来理解和认识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呢?
-、从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
自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大家愈加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应当第一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不仅仅是体现立
法者的意志。离开市场经济的自己规律来人为地根据立法者的愿望而拟定出的法律,势必会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进步。过去大家强调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表现,在经济范围中导致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恶果,足以引起教训。
还市场经济法律以其客观自己规律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法律的第一要义。而把法律看作是客观自己规律表
现的观念,就体现了罗马法中自然法的精神。
彼德罗·彭梵得(PietroBonfante)在他的《罗马法教科书》(IstituzionipDrittoRomano)中说:
“自然法是指‘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法’,而市民法却是‘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的任意创制的
法。’法是意识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它本应一直同它们相符合。很多规范和法律规范准确地符合其目的并同
它相溶合,由于它们只是这一目的的法律确认;但,也有很多规范和规范并不这样,或者是由于它们
已陈旧过时,或者是由于立法者所学会的方法不健全。前一类规范因为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动用途,因而确
实像是自然的产物,并且被叫做自然法;而第二种规范则为市民法。前者同‘正义’和‘公正’永远相符合
;后者则并不是一直如此。”*1这段话对大家非常有启示。中国今天很多的市场经济法律虽然不可以说完全类似彭
梵得所说的“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动用途”的法律规范,但却完全可以说是体现了以反映客观规律为主。它
和另一类主要体现立法者意志的法律是有所不一样的。
法应当体现主观性,还是客观性,还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结合?在市场经济观念提出之前,中国法学界大多
觉得法的主观性是绝对的,忽视了或者说不必论及它的客观性。从英文来看Law,既包括法律,又包括自然规
律的意思;俄文中的закон也是同时包括法律和规律两个意思;中文的“法律”与“规律”同时包括了
“律”这一汉字,这不可以说只是一种巧合。至少可以觉得作为立法者拟定的法律是与客观规律不可以截然分
开,法律精神就其实质来看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但在不同范围中,它所体现的客观性——社会经济
规律性是有所不一样的。
过去大家常常觉得,自然法在罗马法中只指人和动物之间一同性质的一些法则,即“万物本性”。比如在所
有权关系中的先占原则,在男女关系中的自然婚姻等,但,事实上“有不少贸易性规范如让渡、交易等等
也被罗马人称为自然法规范,而它们依旧是人类所独有些。”*21992年通过的《中国海商法》就
是一部极具海商惯例共性的法律。罗马皇帝曾有句名言:“朕诚为陆上之主,但海法乃海上之王。”可见,
皇帝可以根据我们的意志拟定一部统率臣民的法律,但他却不可以任意拟定一部海商法。海商法体现的是各国
人民海商贸易惯例及客观法精神,不是哪位皇帝拟定出来的。
自然法和万民法有很多相同之处,甚至不少罗马法学家视万民法与自然法为同一定义。万民法和自然法势必
要包含世界各民族法律中一同的东西。古罗马时尚的观念是:他们的法律规范由两种元素组成,一半受其特
有些法律支配,一半受人类一同的法律支配。这对大家今天也有非常大启示。市场经济的法律是超越一个国家
界限的,市场已经不是一个民族所能局限的,如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期货买卖法等。这类法律所体现
的自然法精神就是各国这种法律之间的一同规律性。大家需要研究市场经济规律规范中什么是各国法律一同
性的东西,什么是中国所特有些东西。大家也需要一定,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主导方面应是一同性的东西,
亦即客观规律性东西。
体现规律性的法律规范是具备长期、稳定性的,而单纯体现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规范则总是是极易变动的,通
常是伴随立法者的改变或立法者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既然是自然(社会)现象的法律表现
,所以它应是不可随便变动的。当然,从市场交换和买卖的法律来看,不可能有万古不变的规则,那种“绝
对性”是从自然法的精神来剖析,并不是客观现实。但大家过去法律规范变化过于频繁的现象不可以不引起
注意。试问,市场买卖中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交易关系的一些基本规范从罗马法至今的两千多年中
又有什么根本突破呢?大家过去过去突破了,不是又要改过来吗?所以,今天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包含各种
具体合同规范的合同法,也需要体现这种长期稳定的规律性东西。法的权威性来自它的稳定性。
只有反映客观规律性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罗马法著名学者保罗给自然法下的概念是“永远是公正和善良的东
西”*3,就是这个意思。市场经济法律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法律准则绝不可能是正确,绝不可以代表正义,
因此,在推行过程中势必要碰壁。市场经济给大家提出了如此一个新的观念:法律应当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而不止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和武器。
2、从国家到社会
长期以来大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府和绝对计划经济机制下形成了一种国家至上、国家里心、国家意志决
定所有、国家统筹所有的国家本位观念。如此就把社会看作是国家附属物,社会缺少自己的独立性,社会生
活的所有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涉。强大的、无孔不久的国家干涉就是长期以来国内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只
承认公法的存在和否认私法存在的理论基础就是国家本位观念。
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来源于罗马法。严格说来,罗马公法中“公”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定义”。*4那
时候的公法范围也只不过“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5所以,罗马法只不过提出了公
法和私法的划分,但对于公法、私法存在的客观基础还缺少深入的剖析,由于那时国家和社会的离别还不深
刻、不明显。罗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市民社会却还未能充分进步。Civitas一词在中文是多义的,它同时
含有国家、城邦、民族、社会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进步阶段,还很难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严格划分。
但,有些学者在剖析罗马社会时曾说过:罗马是市民社会,而古日耳曼则未历程市民社会。可以如此理
解:古日耳曼当时作为蛮族部落经济,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战争,直接借用国家机器。而罗马社会则充分借
助于产品交换这种方法,不是直接借用于国家机器。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罗马社会是最早形成的市民社
会,而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发达的市民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当市场经济已经作为一定的经济模式和目
标提出来之后,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严肃认真地开始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
法学界提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划分的目的是要论证私法存在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不是私有制;公法存在
的基础是政治国家,而不是公有制。长期以来很多法学家都觉得,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没“公法”
和“私法”之分。甚至有的学者倡导,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所有法律都是“公法”范围。应该说,
公法和私法是相对应而存在的。“私法”既然已经消灭了,哪儿还有哪些单独存在的“公法”呢?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否定公法、私法划分的要紧依据是法学界常见引用的列宁关于否认任何“私法”的论述。经过仔
细剖析研究,列宁原话中即指可以承认私营经济,但否认有任何私营经济关系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干涉。
显然这里谈的不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问题。所以1987年新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译本已将原来的“私法”
一词改为“私的”二字。
不能否认,在今天再讨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不只为时过晚,好像它的局限性也更明显了。但在今天的中国
重谈这一主题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只由于四十年来大家所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
学范围,而且也由于中国四千年来有明文记载的历史中一直是以刑法为本,根本没有什么私法精神。大家
要发扬私法精神就是要补足历史所缺的这一页。罗马法精神就是私法精神,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也可以
说是恢复和发扬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私法精神。
中国正在积极创立现代企业规范,而作为现代企业基本形式的企业的一个要紧特点就是“自治企业”。不赋
予企业真的独立法人地位,不摆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涉和控制,不改变从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就
没现代企业可言!市场经济需要以权利自主、企业自治、契约自由为它的三块法律基石。
公权主要体目前权力,而私权主要体现为权利。大家要论证公法的基础是政治国家,也就是说公权的来源是
政治国家的权力,大家要论证私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无非要说明私权的基础是平等市民。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绝对地说,私法是建构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要承认私法的存在需要承认私法范围中权利是核心,权利是
目的,权利是动力。义务只能具备依从地位。任何私法中义务的履行都是为了达成其权利。而权利一直与其
主体一人(自然人、法人)分不开的。没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无权利的主体。权利本位也就是人本位,
主体本位。在人法、物法、债法的分类中绝不应忽略人法的基础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形态的多元化更使
大家认识到:不赋予市场经济主体以应有些资格和地位,其它法律有哪些用途就会暗然失色。
公法和私法的溶合全方位地讲应该包括两个内容:一方面,国家干涉的面愈加广,绝对不受国家干涉的私法
范围已经没有了。经济法、社会法的出现恰恰是这种溶合的典型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是私法公法化了。
其次,私法精神不断地向公法渗透。私法的自由、平等、人权的精神愈加多地体目前公法范围中。从
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公法私法化了。大家不可以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所以,罗马私法精神的复兴也包含
它在公法范围所体现的精神。
3、从身份到契约
梅因在他的名著《古时候法》中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是对从古时候法到现代法进步过程的高度抽象概括。其
实,更准确些说,罗马法自己进步的历史也是一部“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史。梅因在这部著作中还写道:
“罗马自然法和市民法主要区别在于它对‘个人’的看重,它对人类文明所作最大贡献就是把个人从
古时候社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6罗马法的进步历中就是不断地以个人本位代替古时候家族本位的历史,摆脱
家族权威的束缚而树立个人权利、走向权利平等的历史。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本来是权利最不平等,
但却产生了最能体现权利平等精神的私法来,其缘由在于它的双重性:契约法是自由民之间的平等买卖,而
以家父权为核心的家族法则充满了不平等。体现自然法精神的万民法则不受家父权这种家族规范的约束,罗
马法中市民法与万民法溶合的过程,也就是市民法的家庭本位让坐落于个人本位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罗马法自己就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
假如说罗马自然法对人类文明所作最大贡献就是“把个人从古时候社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话,那样大家
今天也可以说,罗马法精神恢复的一个要紧标志就是把人(包含个人、法人)从身份地位的不平等中解放出
来。这依旧是“从身份到契约”的重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者和企业的先天地位是不平等的,不同所
有制的企业有着不一样的法律调整,享有不一样的权利和义务,承受着不一样的政策待遇和社会负担,这无异于新
的“身份”和“等级”。市场经济立法应当体现“身份”平等的精神,“身份平等”就是真的的契约精神。
大家都知道,罗马法对公法和私法规范的性质有著名的论述:“公法的规范不能由个人之间协议而变更”,而
私法的原则是“协议就是法律”(即私法规范可以由私人的协议变更)。倡导私法精神就是要在中国调整市
场经济的法律中,尤其是在契约法律中规定少量的任意性规范。在计划经济机制下,契约的订立与其
内容均是公法和强制性规范范围。假如契约法规定的越详尽并且都是强制性规范,那样就无异于国家在
替当事人订立合同,其成效恰恰是走向反面。因此,大家正在制定的统一合同法的一个要紧精神就是要恢复
任意性规范的肯定地位。1992年通过的《海商法》第6章“船舶租用合同”的“一般规定”中明确指出“本章
关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仅在船舶租用合同没约定或者没不同约定时适用。”这是
中国契约法中初次以鲜明的任意性规范形式表示出来的条约,因此具备要紧意义。
罗马法有关严格诉讼和善意诉讼有什么区别正是在契约法和任意性规范基础上产生的。相当多的契约,特别是诺
成契约是善意诉讼。在发生这类契约纠纷时,不只凭契约条约,而且还要按善意(诚实)的原则进行给付
,因此,审判员可以不拘泥于契约条约的文字,他有肯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有的契约是严正诉讼,在
发生纠纷时,债务人需要严格根据契约的条约进行给付,审判员也只能严格按契约的约定文字进行判决,他
没“自由裁量权”。这个问题在国内市场经济的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过去相当长期内对于契约纠纷,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常常不考虑协议约定由法官以公平合理为理由而加以改变。今天又有一些法官以严格
的实行契约条约为理由,对这类条约中不适当的部分也不敢加以改变。因此,怎么样把罗马法中解决契约纠纷
的两种不同原则在中国司法中加以体现,具备现实意义。
4、从经验到理性
罗马法是法典化的体系,为后世法典编纂的楷模,罗马法的法典编纂及其理论体系是以高度的理性思维为其
基础的。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说;“罗马人是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的唯理论者。”“
其实是罗马人最早拟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人格权利。”“罗马人主要兴趣是进步和规定
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罗马人对私法的贡献就是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想
。
无论古今中外,立法者都要有两个立足点:一个是立足于社会实质,一个是立足于理性抽象。偏废、忽视哪
一个方面都不可以。每个法律条文都是针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写的,因此它不可以脱离实质;其次,每
一个法律条文又都是行为规范的高度的理性概括的结晶。
罗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义第一表现为法典化。法典自己就是高度理性的体现。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继
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中国是是国内法系国家,社会规范的不同虽然构成了法典化的形式和内容的一些独
特之处,但不可以不承认中国自看重立法有哪些用途以来,其轨迹是沿着法典化的道路前进的。立法是以经验为先导
,还是以理性为先导,在中国并非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只有经验充足之后才能立法”“立法不
能超前”,过去是不少人振振有词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6年的《民法通则》只能按厂长
负责制写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而没办法写入被后来公司法所证明甚为必要的法人机关;只能写进笼统的抵押权
,而没办法写入被今天起草证明甚为必要的抵押权和质权的离别。其实,大家有理性主义作指导的话,完全可
以不必有稍后不久的立法便突破《民法通则》规定的不正常作法。
中国民法的法典化走过了崎岖的道路,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法典化立法尝试都以无结果而告终。80年代初开
始的第三次起草工作也只能以一个“通则”的颁布而结束。是否中国如今社会根本没有拟定一部完整法
典的可能性呢?当然不是。中国立法者高度看重立法的计划性,拟定了八届人大5年(1993年~1998年)任期
内拟通过的152项法律名单。其中有一些是要紧的民事单行立法,如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经纪人法、合
伙企业法等。可以说,立法计划是立法理性主义的体现,但并非主要的表现。更要紧的是,立法内在体系
化的考虑和设计。缺少立法完整体系的基础,仍然没摆脱立法中的“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一个拟定一
个”的旧思路。可见,从经验走向理性,仍是摆在中国立法,特别是民事立法面前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概括,而没抽象概括就没理论。罗马法中的债的规范
、物权规范、人格权规范就是这种高度抽象概括的表现。罗马法所创造的一些规范历经二千余年依旧颠扑不
破,只能说明它是建筑在极为坚实的理论基石上的。中国如今立法的一个问题是:总是容易就一时一事而作
出规定,有时不到十年就失去了意义,这虽然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剧烈有关,但不可以不觉得也和立法缺少深层
次的理论研有关。“重实践、轻理论”是立法的一个深层病害。大家应该从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及其收获中得
到一些启示。
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看重法学家有哪些用途。在罗马法进步的历史中,它的最辉煌的阶段恰恰是著名法
学家辈出的阶段,也是他们在法律舞台大显身手的阶段。罗马法衰亡的过程也同时就是罗马法学衰亡的过程
。在罗马鼎盛时期,法学家就是皇帝立法文件的起草者,从奥古斯都大帝开始,赋予某些著名法学家以“法
律解答权”。过去宣布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和著作具备法律效力。五大法学家对同一问题建议不同时,以多
数建议为准;如不认可见双方人数相等,则以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建议为准,假如帕比尼安未发表意
见时,则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帝国后期罗马法学家的主要活动仅限于举方法学教育和整理编纂法典工作。
可以得出结论说,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在非常大程度上是依赖和取决于罗马法学家的努力。
中国立法中理性主义的增强也是和法学家更多地参与立法活动分不开的。有的法律是委托法学家起草的,其
他则是反复听取法学家的建议。当然,法学家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像罗马法那样甚至可以把著名法学家的著
作视为法律依据,在今天的法制社会中是不可仿效的,但在中国的政治和立法活动中,法学家的地位仍是一
个需待解决的问题。没法学家的地位和用途的提升,就不可以真的达成立法从经验到理性的飞速转换过程。
注解:
*本文原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网站收录于杨振山教授和斯奇巴尼教授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
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本文为作者于1994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罗马法·中国法·民
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所作学术报告。2000年2月再网站收录于《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1,[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4页。
2,[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15页。
3,[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15页。
4,[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9页。
5,《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6,梅因:《古时候法》。
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
点击数:771 | 发布时间:2025-02-06 | 来源:www.lzldqc.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国家人事考试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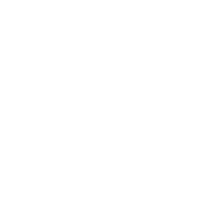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国家人事考试网(https://www.scxhcf.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国家人事考试网微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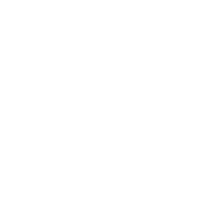
国家人事考试网